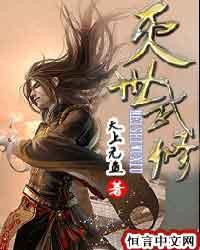三国公孙康第300章 阮籍(下)
化。”文王说:“嗣宗如此悲伤消沉,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,为什么还这样说呢?况且服丧时有病,可以喝酒吃肉,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!”阮籍依旧在喝酒吃肉,神色自若。但他这些无视礼教的行为在当时却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同。
阮籍为人在“竹林七贤”中最为复杂,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。不像嵇康性格“峻切”惨遭横死,也不像山涛、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。他不隐不仕,又隐又仕,官也做,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。谨小慎微,屈己成人,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“全身远祸”之三昧。
阮籍因醉酒以明志,嵇康由绝响而致远;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,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。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!
在政治上,他处于两股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,用一种谨慎避祸、发言玄远、啸聚竹林、借酒遁世的方式才得于生存下来。他素有济世之志,曾登广武城,观楚、汉古战场,慨叹“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!”受家族的影响,他在政治上本来是偏向于曹魏皇室的,对于司马家族的专权行为尤为不满。但是,曹魏家族自从曹丕离世之后,政权一步步衰落下去,司马家族的势力却是渐渐强盛起来。在这种险恶政治环境中,为了生存下来,不得已就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方式,“或闭户经书,累月不出;或登山临水,经日忘归”,终日酣醉不醒,缄口不言。迫于迫于司马氏的淫威,不得不应酬敷衍,做了司马氏的官,当过散骑常侍、步兵校尉。正是采取了这种行为方式,他才得以善终。阮籍的这种政治态度,于他来说是迫不得已的,是苦闷不堪的,我们从他的咏怀诗中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从《世说新语》中的这些记载阮籍言行的片段中,我们可以看到阮籍是个懂得生存之道的人,他虽然心怀大志,但是知道随势而变,谨言慎行,在醉酒中遁世。阮籍是个蔑视礼法的人,他反对的不是礼法的全部,而是其中不合情理的部分。阮籍是个至孝之人,但是他不拘礼于形式,用自己的行为来反抗当权者的“假孝义”。总之,阮籍是生活在世俗生活之中,却“大隐隐于朝”的人,看似怪诞的行为,却折射出一种真性情。
(本章完)
第300章 阮籍(下)